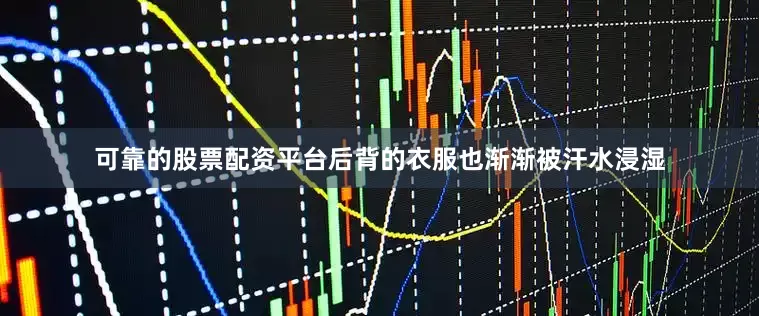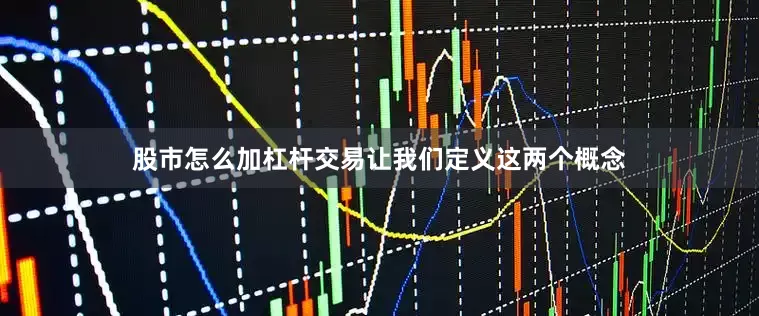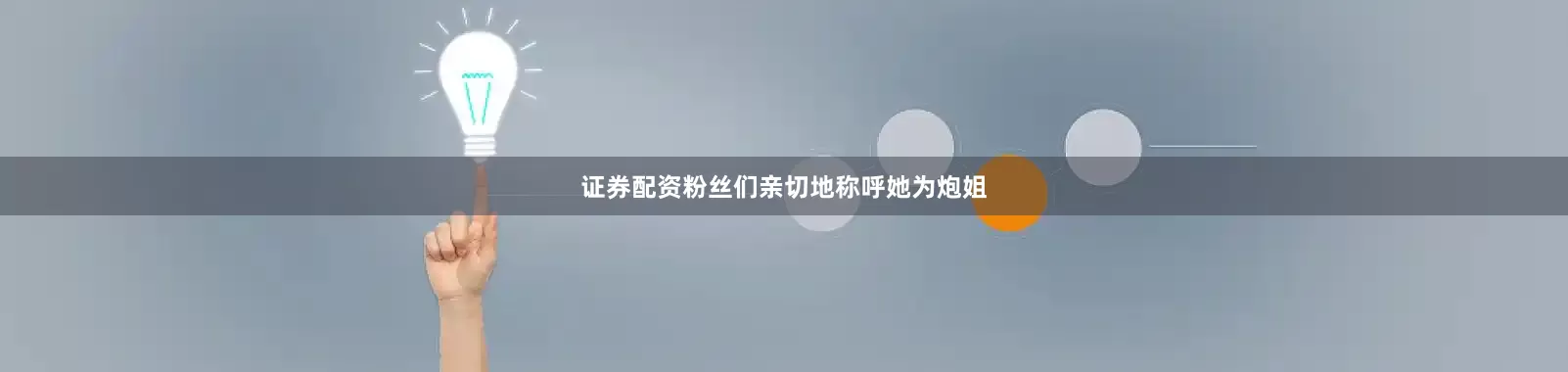他第一次在国外感到不被欢迎,是在柏林。博物馆岛的埃及文物展区,玻璃柜旁的告示牌上写着“请勿触摸展品”,但中文部分被加粗放大,几乎占了整块牌面的大半。德文和英文像脚注一样挤在角落,不凑近很难辨认。工作人员解释说,这是为了“方便中国游客理解”。可他站在那儿,心里却打鼓:既然是不分国籍的通用规定,为什么要单独把中文挑出来、放大处理?他不吵不闹,悄然往后退了两步,却在心里记下了那种被“特别对待”的刺眼感。

以便利之名的单独提示
放大处理中文的,不止柏林一处。跨过半个地球,在澳大利亚的Coles超市,一张醒目的中文告示写着:“每人限购两盒鸡蛋,请勿交换盒中鸡蛋。”字体大得远远就能看见。告示旁边,英文说明并未同样强调。有人忍不住问,难道挑鸡蛋就只有华人会做?偏偏有顾客说,他见过当地白人老太太、印度裔顾客、甚至超市员工也会挑选完整的鸡蛋。还有人半玩笑半无奈地提到,“我就是跟澳洲老公学的,他还教我怎么检查有没有裂。”可牌子只用中文写,难免让人怀疑,这到底是为了沟通顺畅,还是因为某种预先的“假定”。

欧洲大陆的老城市里,此类提醒更像散落在各处的碎片。慕尼黑一处菜市场,把“禁止挑拣蔬菜”的中文提示贴在显眼位置;首尔梨泰院一些餐厅门口,用中文写着“先付款再用餐”,同一家店面对其他国家的客人,却保留餐后结账的习惯——同一规则,分化的执行,悄悄画出了不同语言之间的看不见的线。
行为假设背后的禁令

还有一些告示,语气更像预判。韩国济州岛的海边公园,厕所外只贴着中文“禁止随地大小便”,旁边没有日文、也没有英文;德国一家服装连锁店挂出中文的“八大禁止”,除了常见的“禁止喧哗”,还专门写着“禁止用电水壶煮食物”。有人会点点头承认,有些中国游客确实习惯在酒店用热水壶泡面;可当这一习惯被放在告示牌上,昭告天下并强调国别,多少会令人心里发凉。它不是直白的辱骂,却在潜意识里把某种不体面固定在了一门语言上。
这类告示并非孤零零的个案。在一些旅游季节,“不接待中国游客”、“禁止中国人入内”的粗暴句子也偶尔出现。媒体曾报道,日本有中餐馆贴出此类字样,引发舆论震动与我驻当地使馆的回应;类似的消息进一步加剧了“被区别对待”的现实感。对于远行的普通人而言,这种无声的拒绝,比刺耳的言语更伤人。

偏见是如何慢慢长大的
很多标签不是凭空而来。记忆总偏爱极端。几年前,埃及卢克索神庙里的“到此一游”;东京的公园里有人抓蝉蛹;韩国免税店里购物后留下垃圾——这些画面被反复放大、广泛传播,听者看者反复接触后,心智里便生出一个捷径:不守规矩,等于“中国游客”。但类似的行为,放在更广阔的人群里,并不具有独特性,这一点常常被忽略。

文化差异也在暗中发力。日本媒体曾做过声音测试,中国人在餐厅的平均音量大约75分贝,比日本人高10分贝左右,却远低于韩国人聚会时的120分贝。只是汉语是声调语言,音节清晰、抑扬顿挫,放在安静的环境里格外凸出,于是容易被理解为“吵”。中国的饭桌讲究热闹、氛围,西方的餐桌则强调安静与私密;两种传统各有来历,若缺乏解释,就会被轻易拿来当评判文明的尺子。
媒体放大效应之外,也有统计在悄悄提供另一面。欧洲旅游业协会的资料显示,中国游客的投诉率是全球最低之一。许多人出发前会搜集当地习俗:准备泡温泉前先把身体洗净;进入博物馆主动关闭闪光灯,尽量低声交流。这些琐碎的小心翼翼,很少成为话题;但它们密密麻麻地,构成了日常的绝大多数。

从“被提醒”到“主动做对”的转向
比起反驳,行为的改变更有说服力。去年的世界杯期间,首尔世界杯体育场涌入了近万名中国球迷。比赛散场后,担心有人乱丢垃圾的看法并不是没有,但事后看台几乎干净得像没人来过——许多人自带垃圾袋,把饮料瓶、食品包装装好带走,甚至有人蹲在座位下捡别人落下的纸巾。那一晚并无口号,有的只是默默地把手边的区域恢复原样。

在京都,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游客出行前会仔细研究垃圾分类,甚至自备分类袋;退房时把民宿打扫干净,连床铺都整理平整。在德国旅行的队伍里,走进博物馆会本能地压低音量,碰到不明确的规则先去问工作人员,而不是伸手试探。就连曾经饱受诟病的卢浮宫里,“大声聊天”“闪光灯乱闪”的情况也明显减少,更多人愿意放慢脚步认真看展,而不是匆匆打卡。
制度与风俗:软硬两手的分工

“礼者,禁于未然;法者,禁于已然。”规则的作用,从来是两手并用。早在2006年,中国就出台了《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》,此后建立了“不文明游客记录”机制。如果在国外有恶劣行为,比如乱刻字、打架、逃票等,都会被记录在案;情节严重的,会被列入“黑名单”,影响出境甚至个人信贷。这一套机制并不是要把出游变成紧箍咒,而是提醒人们,迈出国门,也是在代表国家形象。
另接待方的规则同样重要。旅游业的惯例是用统一的告示维护秩序,而不是用对特定语言的放大来暗示某种“天生不守规矩”。在很多国家和地区,反歧视原则强调平等进入与平等服务,商家对特定群体的区别对待会引发法律与舆论风险。换言之,文明的秩序,并不依赖谁被特别点名,而在于所有人遵循同一套明确、可预期的规则。

当彼此走近,误解就会退场
刻板印象改变缓慢,但不是铁板一块。柏林举办的“中国旅游文化周”上,有德国民众第一次听说,吃饭声音略高、氛围热闹并非“无礼”,而是“团聚”的文化表达。理解来自解释,解释来自交流。就像有人说的那样,一万个守规矩的人因为“正常”,难以成为新闻;一件不合规矩的事,却能被当成“全部”。要改变这条叙事路径,除了稳定而持续的良好行为之外,还需要让对方看见“日常的美德”本身。

再看那些“中文专属”的提示
纵观这些案例,可以分出几类:

- 管理型:如柏林博物馆岛“请勿触摸展品”的中文加粗,慕尼黑菜市场“禁止挑拣蔬菜”。它们确实在传达规则,但做法容易让人联想到标签化管理。
- 预设型:济州岛厕所外只用中文写的“禁止随地大小便”、梨泰院餐厅“先付款再用餐”,以及德国服装连锁店“八大禁止”里单列的“禁止用电水壶煮食物”,这些都以行为假设为前提,将某些不良行为与特定群体提前绑定。

- 唯独型:澳大利亚Coles超市鸡蛋限购的中文告示,强调“每人限购两盒鸡蛋,请勿交换盒中鸡蛋”,却并未以同等强度面向所有消费者。考虑到挑选鸡蛋并非某一群体独有,这样的做法更容易引发“不被平等对待”的感觉。
- 排斥型:如“禁止中国人入内”“不接待中国游客”,这类做法跨过了“提醒”的范畴,进入赤裸裸的歧视。相关报道出现后,往往会引发外交层面的回应,法律与舆论成本也随之增加。

这些分类的背后,是同一条脉络:当管理者用一种语言承载更多负面预设时,即便措辞不粗鲁,接受者也难免感到被孤立。相反,如果用统一语言与符号,配以现场人员不带偏见的解释,便能在不牺牲管理效果的前提下,减少伤害。
声音的分贝与文化的分寸

回到声音的讨论。日本媒体的测试给了一个可以思考的线索:中国人在餐厅的平均音量大约75分贝,日本人约65分贝,韩国人聚餐时可达120分贝。把这组数字与刻板印象放在一起,会发现“吵不吵”的印象,并不只依赖物理测量。汉语的声调让短距离交流更清晰,这是一种语言特性;当它进入追求安静的就餐环境,就可能与当地礼仪产生摩擦。看见差异,并在不同场域里调整行为,这不仅是游客的功课,也是跨文化交往的必修课。与之相对,接待方若能提供合理的噪音提示和空间安排,也能让彼此舒适。
媒体镜头之外的日常

“看不见”的一面,往往最值得记下。那些自觉排队、轻声交谈、遵守分类的游客,占了绝大多数。欧洲旅游业协会的统计所言“投诉率较低”,正是对这种日常的间接肯定。倘若镜头总是对准最刺眼的一幕,舆论就会被牵着走;当观众只记得“到此一游”的刻痕,却看不见整理整齐的床铺和干净的座位,偏见就会生根发芽。
从心态到秩序的双向修复

如今,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正在用稳定的自律去抵消过去的偏见,政府与行业的规范也在提供“底线”和“标线”。当个人意识到他不是孤立的个体,而是一张“国家名片”的承载者,很多细节会自然而然地被端正;当接待方意识到,差异不是原罪,统一的规则更有力,许多“中文专属”的牌子就会有更好的替代品:图标化、多语言且等量齐观的提示,加上必要的现场引导。
也许改变他人的看法需要时间,但时间从来不是空耗。那一块块告示牌,终会被更成熟的管理取代;那一张张挑刺的镜头,也终会因为缺乏猎奇而转向别处。等到有一天,人们不再对“中文”三个字额外紧张,而是把它当作普通的世界语言之一,这趟漫长的修复,就算走对了方向。

配资指数网站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股票配资资质瑞银的预测较市场普遍预期高出8%及11%
- 下一篇:没有了